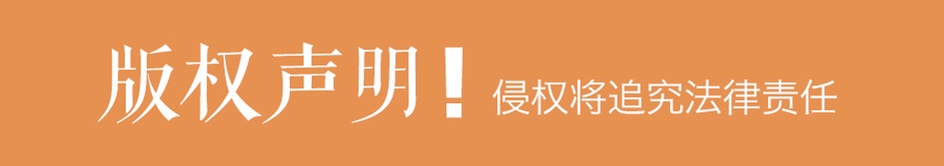求索·學術的意義
“讀研之后,因為我的年齡比較大,同學們都親切地叫我張哥。我們專業只有六七個人,全級只有四十多個人。這時候,我就開始了一些關于鄉土文學的思考和研究。后來我的愛人田錄梅(現為山東師大的教授)也考到了東北師大,我們在一起讀書。當時吉林省招生辦想要一個工作人員,學校就把我推薦了過去。我在吉林省招生辦兼職工作了近兩年。后來覺得自己還是想讀博士,想做一些學術工作,于是我把那份工作辭掉了。”
“在成長過程中,我也有很多的困惑。一個書生能夠干什么?當時的‘三農’問題非常嚴重,我的同學喬煥江說,我們提供不了物質的面包,但我們可以提供精神的面包。我對此很有感觸。于是我的博士論文就做了一些關于鄉土文學的東西。”
“上世紀90年代后,搞鄉土文學創作的人很少,研究的人也很少。如何為我們的兄弟姐妹、我們的這片土地發出他們的聲音來?對他們的生活和命運進行關注,這是作為一個學者的我能做的東西,也是我做學術的意義和價值。”
“讀碩士期間,有次我跟同學王永到東北農村去,漫步于一條荒蕪的河岸。我突然想到做學術的意義,就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和自覺。如果文化是一條大河的話,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條涓涓細流,我們每個人都要匯入這條大河里去,讓這條大河更加洶涌,更加澎湃。我們的生命也就得到了永恒的價值和意義。所以我很堅定地要做一個學者,我的學術本位理念可能是受到了戚廷貴老師的影響。戚老師多次對我說,學術是常青樹,越老越有新的收獲,而且特別自由。我的碩士導師劉雨特別仁愛、慈祥、親切,每次我們去他家里探討學術,他都非常高興。碩士畢業后,我選擇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博士攻讀方向。我的博士導師是逄增玉老師。當時我的博士論文寫完之后,逄老師給我寫了四頁紙的評語。逄老師不僅對我博士論文的觀點、結構提出指導,也對我文學寫作的風格提出了指導,對我說年輕人寫文章不應該四平八穩,應該有沖勁,寫出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思考。這一指導是特別深刻和切中要害的。”
博士畢業后,張麗軍來到山東師大文學院,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教學與科研工作。2008年,晉升為副教授。
“當時寫了很多論文,做了很多學術研究。2008年余華的《兄弟》出版以后,我看了之后不是很滿意,寫了一篇批評復旦大學一些學者對《兄弟》過于推崇的文章,這篇文章影響很大。我跟著吳義勤老師讀博士后、做樣板戲研究,受到很深刻的影響。在山師的這些年,學科許多老師都對我幫助很大。如朱德發老師、魏建老師、李掖平老師等對我都非常提攜。一方面,我為學科和學院做一些工作,另一方面,自己也得到了成長。”
2012年,張麗軍成為山東省作協首批特約研究員。2013年,被聘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二屆客座研究員,同年晉升教授。2015年,被聘為山東省首批簽約文藝評論家,遴選為博士生導師,被學校任命為文學院副院長。
“文學滋養我們的心靈,讓我們的內心充滿愉悅感。”張麗軍笑著說道。
“在帶研究生的過程中,我覺得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平臺,對我很有吸引力,而且也比較自由,內心有一個比較寬闊的精神空間。我這些年所做的研究包括鄉土文學研究、樣板戲研究、老舍研究,這些研究可能都與我內心有關系,與我的關注有關系,與我農村長大的經歷有關系。這些研究對象都是某種意義上的弱勢群體。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我有責任、有義務要把他們被遮蔽、被壓抑的聲音呈現出來,把他們的痛苦呈現出來,和他們一起追求一個幸福的、自由的、公正的生命空間,一起追求文學的正義、文化的傳承與生命的真理。”
守護一份心靈的平靜,守望一方文學的凈土。在張麗軍看來,這就是他作為學者的意義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