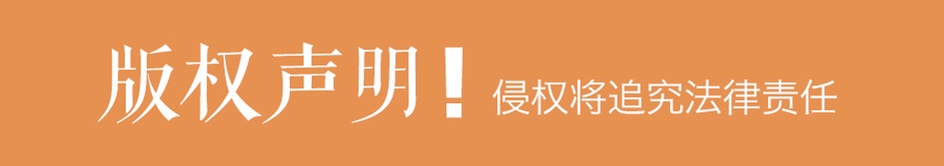仁術勤和:“我自豪,我是莒縣人”
“每當有人問起我是哪里人,我都會自豪地說,我是莒縣人。”1月19日,面對家鄉的記者,王莒生道出了自己的心聲。
王莒生,原首都醫科大學北京中醫醫院院長,首都醫科大學中西醫臨床醫學院院長。1948年,王莒生出生于莒縣一個革命軍人家庭,父母轉戰南北,孩子生在莒縣,就給孩子起名“莒生”,因為還要繼續征戰,就把她寄養在一對農民夫婦家里。解放以后,她才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青年時代的她插過隊,當過赤腳醫生;后來當了兵,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再后來進工廠,當過工人。擁有農民養父母的特殊經歷,以及插過隊下過鄉,當過兵扛過槍,進過車間當過工人的豐富閱歷,使她和百姓有一種天然的情感。正如她所說:“我曾經生活在社會最基層,整天和農民、工人、士兵們一起干活。我了解底層老百姓的艱辛,懂得他們的語言,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作為醫生,我最崇高的理想就是當一個受老百姓歡迎的好醫生;作為院長,我最美好的愿望就是能夠培養出一大批受老百姓歡迎的好大夫。”
難怪患者總是親切地稱她為“我們的平民院長”。
從小就有一種“莒縣情結”的王莒生,隨著年齡的增長,現在這種情感更濃了。王莒生說,家鄉浮來山上有棵近4000年的銀杏樹,因為有極好的水土滋潤,始終昂然挺首,寬厚的胸懷蔭澤后人,頑強的生命力孕育累累果實,這些都是“莒縣精神”的時代象征。“最享受人家叫我王老了。”面對鏡頭,王莒生不失幽默地調侃:“人家稱呼你老王,說明這個老人姓王。王老就不同了,說明姓王的老者是有技術、有特長、有影響力的人。”
在北京中醫醫院的大門左側的墻壁上有四個鎦金的大字:仁術勤和。這是醫院的院訓,是王莒生親自參與制定的,當時院里還專門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最終采納了王老的方案。
王莒生詮釋了這四個字的涵義:仁,仁德,當醫生的首先要有仁心;術,技術,醫生沒有好的醫術是不行的;勤,勤勉,業精于勤,天道酬勤,這個勤字還有勤儉的意思,不能鋪張;和,和睦,家和萬事興,院和方能成大器,中醫流派最重要的就是和氣,各自為政不行,要相互滋養。“這兒可是塊寶地啊,以前是公主府,慈禧太后干女兒住的地方。”王莒生指著窗外不遠處的北海公園白塔,言談間不無自豪。
有一段時間,在王院長的診室里,有一個特別奇怪的“景觀”:一位中年婦女,不看病,拿個板凳坐在旁邊“聽”王院長看病。問她為什么,她說:“聽王院長看病,心里敞亮,沒吃藥,病就去了一半。”
王莒生介紹,中醫看病歷來注重情志治療,既看“病”,更看“人”,治病求本,講究整體觀念,辨證論治,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按照老百病的說法就是要去“根兒”。別看患者得了皮膚病,好像病在“皮兒”上,其實往往病因在“瓤”里。很多皮膚病實際上是一種心身疾病,需要醫生進入患者的內心世界,能和他產生共鳴。
為了掌握心理學專業知識,加強與患者的溝通能力,已是主任醫師的王莒生利用三個月的周末時間去安定醫院參加心理醫師培訓。教室設在沒有電梯的簡易樓里,幾十節臺階對患有關節炎的她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克服困難,中午啃塊面包,下午繼續上課。王莒生說,“交流是一門藝術。和患者交流,一要看病,二要看人。年齡、性別、職業、性格不同,人生當中走的階段不同,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疏導方式也因人而異,既需要把握時機,又需要把握好分寸。”
臨床上,什么樣的患者都有,有的是叛逆的孩子,有的是煩躁的更年期女性,有的是失戀的年輕姑娘,有的是落寞的退休干部……不分年齡,不分貴賤,不分職業,王莒生都會耐心地和他們交流,試著讓患者打開心扉,解開心結。在和患者溝通的過程中,王莒生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時候像是母親,有時候是患者的朋友,有時候又像是下級……“當事實無法改變的時候,就選擇接受;用健康追求身外之物不值得。”憑著她的愛心和豐富的人生閱歷,總能把話說到患者的“心縫”里去,讓患者愛聽、“受用”,既能讓患者有很好的依從性,提高藥物治療的效果,這就是老百姓常說的“心病還需心藥醫”吧。
王莒生是中央保健局會診專家,也是老百姓評選出來的首都健康衛士。她說:“中央保健是執行特殊任務,為百姓看病是一生天職。”在她眼里,沒有貧富貴賤,沒有高下之分,統統是病人,一視同仁。這和她的經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